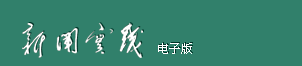| 郑宇丹2110-11-1
记者的人脉思维异化并非全部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其中包含了政治、经济、大众乃至技术的多重制约,尤以互联网文化和权力寻租的现实环境所起作用最大。不能说人脉思维的异化等同于伦理的退化,但从社会影响来看,异化了的记者人脉思维还是会制约媒体公信力的提升、独立性的坚守和公共性的捍卫。因此,重构新闻人的社会身份,建立以问责为主的自律机制是媒体自我矫正的必然路径。
今天,在记者赖以生存的动力舱中,互联网文化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景观。它不仅以强大的技术整合力改变了传统媒体的编写手段,更以惊人的文化渗透力颠覆了传统记者的思维模式。普利策般的“守望者论”及邹韬奋、范长江等理想至上的精神光芒,正被异化为默多克般的实用、效率与权力。尽管依旧有大量的媒介工作者践行着新闻的公正与良知,但在新闻娱乐化及媒介趋同化影响下,理想越来越容易被趋势所遮蔽。如同学者支庭荣所言:世界是平的,媒体却凹了。
互联网文化影响下,整个世界都是平的,人人都可能是记者,这是当下新闻人遭遇的第一大生存困境。与此同时,转型的中国,百舸争渡,鱼龙混杂,尤以权力寻租现象令人发指却又屡禁不止,这也对记者的正常化生存造成了很大影响。
一般认为,权力寻租是政府各级官员或企业高层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避开各种监控、法规、审核,从而寻求并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腐败活动。其实,这只是狭义上的理解。社会学家詹姆斯·S·科尔曼认为,社会系统由“行动者”和“资源”两部分组成,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面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①就此意义来讲,包括记者在内的绝大多数工薪阶层都生活在泛化的权力寻租语境下。
由于大多数媒体采取的是以量化指标为主的绩效评估体系,记者的工作如同工厂的流水线,只有多发稿件,才能更大效益地利用媒体稀缺资源(新闻发布渠道),获得生存收益。然而,记者工作的特殊性又使得他所生产的内容未必完全获得通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权力团体的左右,包括政客、财团、广告主等。这就使得记者的生存处于广义和狭义的权力寻租双重制约下,生存困境可想而知。
今人面对的是比工业革命更显复杂的时代,记者的生存面临着互联网文化与权力寻租的双重制约,这势必促成一种新式思维的诞生。尤其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建构方面,新的人脉思维已然将“水门事件”中伍德沃德与“深喉”之间实证、永久般的共同体关系异化为虚拟、即时的利益关系;将五四时期《新青年》的“同人”气质异化为边界分明的“圈子”文化;将史量才、邵飘萍等人的正义选择异化为所谓“理性经济人”的角色。具体表现为:
虚拟式交往
受互联网及新闻娱乐化的影响,当下的新闻作品越发地呈现出不完全倚重事实和逻辑关系的非线性特征。以默多克为代表的小报干预主义风潮已然形成当代的大众文化。这种文化以大众趣味底线为标准,具有可复制性、消遣性、一次性消费等特征。当代大众文化的席卷范围是全球性的也是全媒体的。美国媒体和公共事务中心近年所作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三大新闻周刊的新闻力度都在软化,娱乐新闻和名人传闻的内容增加了一倍,连最受尊敬的《时代》周刊,如今也用1/3的版面来介绍无聊的娱乐信息了。
中国媒体亦不能幸免甚至有更强烈的娱乐化诉求:因受制于政治与商业双重束缚,只有娱乐是最安全的。于是乎,选秀、征婚、传奇等一系列大众化栏目风起云涌,新闻也日益走向娱乐化:腐败背后的情色故事,拆迁过程中的自焚场面总是占据大量篇幅。
因此,记者在获取新闻的时候,更看重时效性、冲突性、趣味性和话题性等价值,而对支撑新闻的事实环节不再像传统做新闻那样精益求精,对新闻消息源的依赖也不再像报刊时代那样牵系紧密。
新闻界前辈邓拓在谈到交往时曾经说过,记者要和各方面的知心朋友共休戚、通血脉。这是传统人脉思维的支撑点,如同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界定的“共同体”。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互联网时代,记者的人脉思维更像是滕尼斯所认定的“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田园牧歌般的诗意关系已土崩瓦解,更加受制于技术的聚合。这也是为什么facebook、youtube、人人网等社交网站备受欢迎的原因。
大趋势之下,记者的交往手段也日益走向临时的、匿名的、随意的对话状态,而当下流行的六度分隔等新型交往理论也使得这种手段获得了理论与技术上的支持:既然六个人以内一定可以找到自己要找的消息源,又何必纠集于同少数交往对象的“忠诚关系”?中国文化本不是一个重视“实证”的文化,在科学启蒙尚未完成的当下,记者人脉思维的这种偏向,对媒介的公信力将造成很大程度的侵蚀。
圈子式经营
传播学家盖伊塔奇曼认为“新闻生产网络”依据三个前提:受众只对发生在某些地点的事情感兴趣,只对某些组织的活动感兴趣,只对某些话题感兴趣,从而形成收集新闻的三种制度:地理边界化(不同地区媒体采访侧重区域不同)、组织集中化(每个部门及记者“跑线”不同)、主题专门化(每个版面或栏目内容不同)。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大多数的记者都生活在一定的圈子里:地缘圈子、人缘圈子、话题圈子。圈子的存在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也是每一次腐败案发,总是一串人受到牵连而不是一个人。如发生在山西繁峙的金矿爆炸案,就有11名记者接受贿赂。而当下的互联网文化无疑也是一种圈子文化。用户从事个性化搜索、论坛化交流、手工化生产,都是在一个个自我选择的圈子里寄居。
互联网文化的圈子加上权力寻租的圈子,使得记者往往处于一种集体爆发或缄默状态。集体爆发类似于对新闻的密集炒作,而集体缄默比炒作更为可怕。例如三鹿奶粉事件,在东方早报记者率先捅破窗户纸之前,地方媒体保持集体缄默达1个多月之久。不知道是地方政府保密功夫做得好,还是媒体新闻挖掘能力实在有限,连消息灵通的网络都未见一丝匿名的风声。
可见,记者的各种圈子乃至由此而生成的圈子文化不仅存在于与政治资本的周旋中,也在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交互中或缄默、或妥协、或中途退场。此类的圈子文化必然导致媒体的公共性存伪、独立性遭到消解。
功利式选择
在当下中国,有一种理念私底下流传。该理念打着“理性经纪人”的旗号,错误地解读着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曾经获得诺贝尔奖,它的本意是强调市场调节,减少政府干预,从而防止权力寻租。而错误流传的理念只强调该理论对人性的假设:人都有自利的一面,有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倾向,即“理性经济人”本色,从而为权力寻租的正当化寻找借口和心理安慰。
在新闻界,也不乏这样的观点。金元新闻、御用文人、商用文人的不断涌现,就是某些记者所谓“理性”选择的结果。可悲的是,这种理念正在大众文化的伴奏下向主流思想迈进。尼尔·波兹曼是较早看到这一趋势的学者,他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不无忧虑地写道:“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大家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②不难看出波兹曼语义中的双关意味。他一方面惊叹于电子媒介的摧枯拉朽之力,一方面为当代人在责任与功利之间选择的高度一致性无可奈何。
在人脉交往的功利主义思维引领下,记者“权力寻租”现象的出现也就见怪不怪了,主要表现为或吹捧报道对象换取经济利益,或假曝光之名威胁、敲诈报道对象。新闻出版总署近年来频繁曝光的记者站腐败现象便是对功利主义倾向的声声警钟。但为什么“权力寻租”在媒体依旧屡禁不止,新闻学者展江教授试图用制度经济学解析这一现象。他认为,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这就是路径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③
这或许就是功利主义能够成为经典经济学基础的原因。“在贪婪的惯性轮下,经济意义上的人成了整体意义上的人,惟一的人”④,媒体和它的记者们也很难免俗。或许人脉建构本身就是一种功利的行为,否则也不会有这句话的盛行:“一个人能否成功,不在于你知道什么,而是在于你认识谁。”这不是某种行业的堕落,而是整个世界的现实宿命。
制度式寻租
笔者认为,将发生在新闻界的“权力寻租”现象仅仅归咎于少部分人的道德沦丧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记者借助媒介组织的既有资源进行“权力寻租”,已经逐步呈现出常规性、普遍化的态势。而这一态势正在成为媒体制度化的一部分。诚如一位资深新闻记者所言,当前中国记者权力寻租现象已经是制度性的,因为对记者收入的设计或多或少考虑到这个因素,也就是说记者的劳动价值等于记者的公开收入加上可能获得的红包收入。新闻学者陆晔、张志安亦认为,通常的“车马费”或价值两三百元的“红包”,往往被媒介行业视作普遍的潜规则或新闻生产过程中消息源支付的必要成本,成为上下默许、南北通行的职业习惯,这种默许等同于重新界定了新闻人的伦理边界。⑤即便有不少媒体进行自我的制度化矫正,但这样虽然表面上遏制了记者的个体寻租,实质上是将个体寻租演变为集体寻租,依旧等于默认权力寻租的制度化。
由此可见,当我们在谈论传统媒介的影响力正被网络消解的时候,仅仅看到了问题的一个向面,即技术文化的层面,却忽略了伦理文化的功用。掌控着采访权等稀缺资源的传统媒体日益走向衰落,绝不可能只是外因使然。监督作用的缺位、伦理边界的模糊正在让它们自食其果。
自恋式传播
谈到新媒体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当下的主流声音是,这一变革并不在于精英与草根的权力转移,而是“你”到“我”的权力转移。大众草根的崛起,在消解和替代传统精英的话语权的同时,又在互联网创造了新的“知本新贵”。精英和草根都只是身份的区别,其核心都是自“我”特性,都需要通过互联网的力量来赋予自我权力。
在这样的情势下,代表着传统精英话语权的传统媒体并未完全意识到“我”权力的势力改变,而是依旧处于“我”对“你”说、“我”说“你”听的传统思维模式,依旧呈现出自恋式的自我狂欢,显然没能谙熟互联网时代“我”权力流动的规律:即你能不能创建与这种新技术工具相适应的新观念、素质、价值和技能?你会不会用这种新技术和新人文持续地构建自“我”特性?如果不能,记者乃至媒介的自恋式传播思维很容易被颠覆。
近年来频传的记者被打以及当事媒体大炒特炒的现象,一方面显示新闻职业的神圣性、权威性遭到抵制,一方面也显示出记者“你必须配合我”这种传统思维的现实贻害。习惯于超越新闻事件的当事人而自己成为主角,是一部分记者乃至媒体依旧没能走出的误区。互联网时代,当国家、家庭、文化、地域这些曾经强势的社会束缚力量都在个人主义复兴的过程中遭到削弱的时候,媒体自然不能幸免,网络也并非特例。网络之所以笼络越来越多的个体,并非它是权力本身,而是它提供给人们施行自我权利乃至权力的平台,它越来越像约翰·弥尔顿所向往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在嘈杂的纷争中达成“真理”的自我辨识。这是网络胜出传统媒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只提供平台,而把表演权交给登上舞台的一个个“我”。
并不是说“记者”被打不值得同情,乃至作为一个新闻事件得以传播,而是要看到这种传播模式背后客观性的缺位、媒体资源的自我占据。这也是传统媒体在网络面前败下阵来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记者的人脉思维异化并非全部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其中包含了政治、经济、大众乃至技术的多重制约,尤以互联网文化和权力寻租的现实环境所起作用最大。不能说人脉思维的异化等同于伦理的退化,但从社会影响来看,异化了的记者人脉思维还是会制约媒体公信力的提升、独立性的坚守和公共性的捍卫。因此,重构新闻人的社会身份,建立以问责为主的自律机制是媒体自我矫正的必然路径。
当然,我们更期望媒体所栖身的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环境的自洁,其中包括打通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督的壁垒,达成对权力寻租的立法约束,保障记者的合法权利等。
路且漫长,但总得有人在路上。
注释:
①詹姆斯·S·科尔曼著《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②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③展江著《记者站腐败的制度分析》,《财经》杂志总160期,2006
④詹姆斯·凯瑞著《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
⑤张志安、陆晔著《记者“权力寻租”中的社会资本转换及其伦理边界》,《国际新闻界》,2008
(作者: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暨南大学新闻学博士生) |